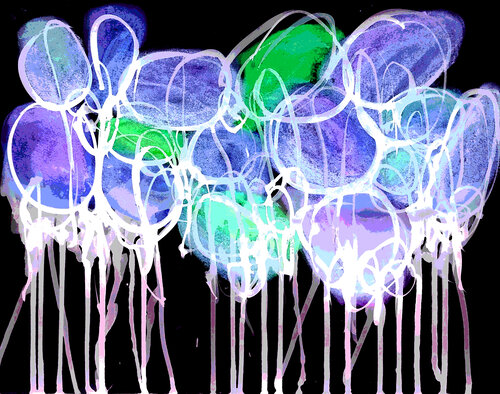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如家尋覓—子圓的女性視點和空間
第一次看《但願人長久》到了中段時,我一直想到夏洛特威爾斯(Charlotte Welles)的《日麗》(Aftersun)(2022),故事講述11歲的蘇格蘭少女蘇菲與父親在土耳其渡過的一個暑假,電影用了撿拾、拼接記憶的敘事手法,重塑女主角兒時對父親的追憶。不過,《日麗》只不過擷取少女生命中某個時刻的橫切面,有如一篇短篇小說,《但願人長久》卻橫跨了香港回歸後的20年時間,是導演祝紫嫣帶有自傳性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和「成長故事」(Bildungsroman),理應是長篇小說的格局,但同為編劇的祝導演巧妙地以1997年、2007年和2017年三段時空的橫切面築起故事框框,講述來自湖南的新移民林子圓和妹妹林子缺二人在香港成長經歷,由六位女演員飾演的兩姊妹在這三個階段角色,其中以姐姐子圓的主觀視野重構三段時期兩姊妹的回憶及他們與父親的關係,從而側寫香港二十年來的變遷,頗見匠心。
有關回歸後新移民的電影,我們會想到陳果的《榴槤飄飄》(2000)和許鞍華的《天水圍的夜與霧》(2009),《但願人長久》卻具有香港電影少見的歷史和時間幅度,但不以什麼大事件為經緯,而是從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感性經驗來呈現出新移民/新香港人的心路歷程,以本地人/外來人的辯證目光,透視新移民與香港這個稱之為「家」的地方那若即若離的情感聯繫。
電影多次以女主角的主觀鏡頭喚起複雜的認知和情感反應,而重複出現的場景更是誘發情緒和記憶的載體。1997年,8歲的林子圓(許可兒飾演)初來步到,蹲在路邊等著見爸爸,留意到路人一雙雙光鮮潔白的波鞋,最終見到爸爸也穿着白色波鞋到來。事實上,我要等到第三次看電影時才察覺到主觀鏡頭呈現子圓視覺下的白鞋子的箇中意味,和在她身上所喚起的感性回憶。
祝紫嫣在一個訪問中談到她小時候初到香港的第一個印象,當家鄉的人們都是穿涼鞋時,在香港街頭,人們都穿着一雙雙潔白的波鞋,是乾淨而沒有灰塵的。她又提到童年時坐過逸東酒店的玻璃電梯(我們俗稱的「子彈𨋢」),一家三口在密封而透明的空間,看見外面的夜景和萬家燈火,感覺短暫的幸福時光,原來這就是香港。在電影中,子彈電梯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當子圓跟爸爸媽媽搭上透明電梯,看見香港的夜景; 第二和第三次是長大成人的子圓(竹紫嫣飾演)在日本當導遊乘搭當地城市的地標透明電梯,電梯門關上,隔絕了外面的噪色,其密封和抽離的空間勾起她童年時侯的「感性記憶」(affective memories )。

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學者段義孚(Yi-Fu Tuan)強調我們要重視人與空間和地方的「情感聯繫」(affective bond),他的理論着重身體感知、情感記憶如植根於人處於空間和地方的個體經驗和情感交流。他分析「空間」(Space)的概念是比較抽象、開放和自由,但又可以是隱藏着危機;「地方」(Place)則是安全、穩定。換句話說,人們(新移民) 會為他方的空間賦予意義,重新定義本來無意義的場所,努力將「空間」轉變成自己的「地方」。
可以說,子圓一家對90年代的香港有着自由和開放的憧憬,當中意味著流動性、行動、自由、潛力、未來。父母都渴望城市可以成為一家人謀求美好生活的「地方」。可惜事與願違,人越嚮往高處,「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子圓一家窮困,只好窩居在狹小幽暗的唐樓板間房中。電影另一幕呈現小孩最深刻的回憶,是一天她放學回家後爬上閣樓,看見父親林覺民(吳慷仁飾演)躲在裏邊吸毒。
在大學年代我讀過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The Poetic of Space),印象最深刻的是哲學家相信我們童年居住的房子灌注了棲居者的情感、遐想與想像,當我們登上充滿幻想的閣樓時——我們看到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抱負和夢想。真的嗎?我想子圓會這樣問。對青年時代的林子圓(謝咏欣飾演),狹窄的斗室滿戴她與父親發生暴力衝突的記憶,爸爸吸毒、偷竊、入獄,媽媽(周琳飾演)改嫁,家已走向支離破碎。她渴望走出去外邊的「空間」與她的男友建立一個新世界,她嘗試好像童年時跟着父親一樣的追隨他,可惜男友不過是窮困的邊緣青年,對生活迷失而不知所措,喜歡高買,最後更變了心,對她暴力的摑了一巴掌,完全重複了他與父親之間不快的經驗。電影的英文譯名用上的愛情老歌Fly Me to the Moon變成最大的反諷 :「帶我飛奔往月球,讓我在星間玩耍,讓我看看春天是甚麼樣子,在木星和火星上。」長大後的子圓從事導遊工作,既是生活所需,也許是尋尋覓覓,在其生命不斷移動中的「暫留」(pause)所到之處,仍然找不到一個安身的「地方」。
吾家何處—子缺的在地情結
香港電影一直不乏有關父親的題材,但大部份都是關於父子關係,並流露傳統儒家社會的家庭倫理價值觀,例如中聯製作,吳回的《父與子》(1954),以及左派鳳凰公司支持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直到比較近期譚家明的《父子》(2006),頗為顛覆了父親的形象,而且故事發生在馬來西亞,予人一種父親被放逐的異味。
《但願人長久》 第一個鏡頭是林覺民剛出獄後乘船回家,他的憂鬱面容置於鏡頭的下方,良久不動,彷彿他一直只能在社會邊緣徘徊、掙扎,大半生人都出入於監獄與已經不屬於自己的家,因為他失去了作為父照顧兒女的能力。電影開始時,我們看見他從海上來,就好像呼應了結尾一段我們知道他是偷渡來港——是從水路還是陸路?他又說過年青時在家鄉湖南是游泳高手。(劇中提到他的一個同鄉叫越南仔,死後朋友只能把他的骨灰撒在大海。)林覺民一生都在輾轉漂泊,無家可歸,出獄回家後兩個女兒都疏而遠之。影片最後一個鏡頭,是林覺民跟子圓最後道別,他回眸一看,女兒已經消失於其視野之中。
影片得力於張叔平協助剪接,能夠簡約地在主角生命中幾段重要時刻,記錄女兒對父親的回憶。第二幕結束之前,子圓在窗戶外看見父親在路上匆匆離開的身影,跟著要等到十年後兩父女才得以再相見,但很快就天人永隔。兩姊妹得知父親悴然離世,電影只用了兩個鏡頭輕輕的交代她們在房間啜泣。「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父親死後子圓回到湖南家鄉,才發覺他一直念茲在茲的那片百合花田早沒有了。
《但願人長久》可以解讀為新生代在缺乏父母一輩的引領或保護之下,漸次疏遠傳統家庭的價值,疑惑於吾家何處,揚棄所謂「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而更重視人對家庭和社會的「認同感」(sense of identification)。劇中妹妹林子缺反映了「異鄉人」的心情,嘗試擁抱多元的普世價值,走出狹隘的本土主義。中學時代的子缺(許恩怡飾演)努力融入香港菁英的學生群,也對遭到好友排擠和歧視的新移民同學伸出援手。長大後的子缺(袁澧林飾演)對老父孝順有加,劇中更隱晦的交代了她曾經參與本土的抗爭運動而可能被檢控並鋃鐺入獄。子圓和子缺,一個月亮的兩面循環:一個是望極天涯不見家,一個是風雨飄搖,叩問鄉關何處。

本來,我想連帶一起討論許鞍華的《客途秋恨》,但篇幅所限,於此唯有以記錄片《好好拍電影》中許鞍華的一段訪問回答作結:
「整天都覺得,怎麼說的要定自己的身份。香港本身的電影工業,依附在合拍片的中國的電影工業中。我們這一代人,都在問自己身份的問題。後來覺得我們不做這事情了,我們做世界公民吧。但現在的人很討厭全球化,說又要找回自己的文化。那就很矛盾了,那些又屬於自己的文化呢?那就很難定義了。」
「我不走,我要留下來,將好好的拍好電影,記錄這個地方的人和事,和記錄這個地方發生的變化,我很好奇,我想知道。」
許鞍華接受這段訪問,時值2017年,剛好是《但願人長久》的成長故事作結的年份,而妹妹子缺的命運仍懸而未決。
延伸閱讀: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段義孚: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潘桂成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The Poetic of Space),龔卓軍、王靜慧[譯],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3月。
許鞍華[導演], 吳念真[編劇]:《客途秋恨》,高仕電影公司中央電影公司聯合出品,1990.
文念中[導演] :《好好拍電影》,台北 : 嘉勳實業,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