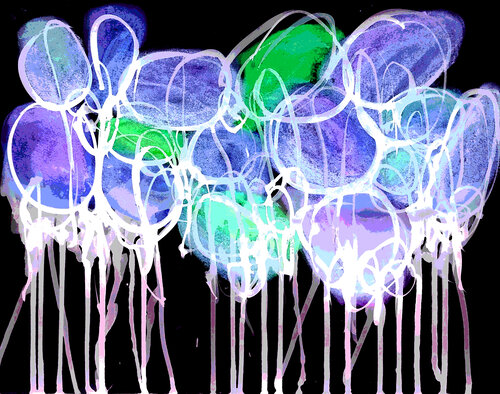一條褲製作Pants Theatre Production 四月下旬在高山劇場,一連三天上演了改編自美國當代劇作家Doug Wright 的舞台劇本Quills,中文劇名翻譯為《撒旦狂筆》,「撒旦」其實取名自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1740-1814),一個在文學史上最藐視人類社會規範與道德的作家,及其行為與寫作上大膽挑戰男女身體與愛慾的底線,相信大部份未讀過他著作的人,已聽聞過Sadomasochism,即 S&M「性虐/被虐」的名稱就是取自他的名字,甚至被稱之為「蕯德主義」。

不過,Doug Wright 本身的劇本,更多是要探討藝術與道德、創作與審查的微妙關係。根據劇團的導讀文章,《撒旦狂筆》於1995年在美國華盛頓首演,及後搬演到紐約百老匯的舞台。劇本創作的原因,源自當時美國政府對藝術家創作自由的打壓。1980年代,美國的國家藝術基金會不斷受到眾議院參議員在撥款上的壓力,禁止基金會使用政府的資金協助宣傳、傳播及製作淫褻或不雅的藝術作品,其中包括虐待狂、同性戀、及詆毁特定宗教的藝術作品,並表示有關的作品可悲和低俗。是次風波引起Doug Wright 的注意,他認為藝術就是應該服膺藝術的宗旨,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思想及創作自由,因為這次事件的風波,促使編劇重新詮釋侯爵的離經叛道行徑及其異端邪說,以古諷今,表達對政府對藝術自由打壓的不滿。
薩德出生於法國南部的貴族家庭,家境豐厚之餘,對法國的文學和哲學有着深厚的認識,但他對於當時將伏爾泰 (Voltaire) 等大文豪和哲學家等作為法國文化以至歐洲啟蒙運動的代表,不以為然。薩德其人恃才傲物,生活放浪形骸,年青時過着荒淫無道的生活,創作上亦在實踐記錄自己以及法國貴族放蕩的私生活為主。薩德深知上流貴族的卑鄙和醜陋的面貌,包括教會、法庭、軍人、以至富商,對其令人讀來噁心的變態性行為,及貴族權力的腐敗,描寫精準而且細緻,極盡諷刺之能事,筆者或稱其作品為「黑暗現實主義」。薩德將自己的激情如山洪暴發般的傾注在情色文學 (erotic literature) 的創作之中,無視當時社會和宗教的道德約束,歌頌身體和感官上的愉悅及享樂主義,不愧為當時法國的放蕩主義 (libertinism) 和浪蕩子文學 (libertine literature) 的一代宗師。

薩德其人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曾有好幾次鋃鐺入獄,甚至因為法庭判定為道德淪喪的惡行而被判死刑,但最終他逃獄出走到意大利。不過,薩德一生其實有多達29個寒暑都在牢獄或精神病院中渡過,幾乎占了他生命中的一半時間,而封閉的囚室空間便成為了失去了自由的薩德最終的寫作實驗室。1777年,他被關進了森嚴的巴士底 (Bastille) 監獄。而在這監獄的五年半光景中,剛好是蕯德寫作的另一高峰期,創作力非常旺盛。因為其貴族的出生,薩德獲得好多優待,在監獄內他可以隨便讀書和寫作,著名的《索多瑪120天》等著作都在獄中完成。
就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生,革命群眾攻陷巴士底監獄之前,蕯德剛好被轉移至精神病院,此時他的妻子決定跟他離婚。大革命後薩得曾經重獲自由,因為貴族出身的他卻支持革命,並曾經在新的共和國中當選過國民議會議員。但是由於薩德繼續創作及出版的作品,暴露了當時貴族階級的奢淫奢想和無法無天,激怒了特權階級,被當時法國元首拿破崙譴責為淫蕩和厭惡之極,薩德在未經審判下,以文入罪,再次被拘捕入獄。
薩德最後在1803年被關進了查朗頓精神病院 (Charenton Asylum),在此渡過餘生。《撒旦狂筆》的故事,就根據薩德在此病院的經歷再行創作,以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時期為背景,劇本提及法國階級鬥爭、巴士底監獄事件、及血腥統治時期 (Reign of Terror) 的大屠殺。劇作家遊走於虛構與現實之間,自由發揮,借薩德之口和筆,抒發作者對藝術及言論自由表達的憂慮與及堅持。

全劇的精彩之處,在於通過人物的互動、矛盾、以及唇槍舌劍,來突顯藝術作品與讀者及審查機關之間的張力和關係。古米亞神父 (Abbé de Coulmier) 一心想要改造薩德的言行和思想,懇求他不要再講下流的故事。他成為了薩德忠實的讀者、評論家、編輯、及道德審查官。薩德強調的是讀者在藝術作品中的自身體驗,作家只能提供觀能和智性上的刺激,他所能控制的只是藝術手段本身,而作者根本無法控制讀者的反應。薩德自辯,他只是擷取本來就是充滿仇恨和嗜血的現實生活,他不過是記錄事實,而且盡職盡責。作家不過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Pandora Box) 的狹小空間。讓長着翅膀的惡魔回歸本來屬於他們的一個紛亂的世界。
劇作家通過薩德雄辯滔滔的說辭,作出現代主義的宣言:藝術與文學作品不應該跟社會道德扯上關係,更加不需要擔任道德教化或社會改革的重任。薩德認為,其作品只不過為讀者提供娛樂,在生活上微不足道,審查員根本不用小題大作,視其為會危害倫常道德的論文,而進行諸多限制,甚至扼殺。
薩德堅持自己寫作的是娛己及娛人的作品,在洗衣房中工作的瑪黛蓮 (Madeleine) 是侯爵的「粉絲」,代表喜歡品味「庸俗」和誨盜誨淫故事的大眾讀者,他的瞎子母親最愛聽女兒讀出薩德所寫的淫邪的故事,有如中國讀者喜歡偷偷看《金瓶梅》,而不是四書五經。
事實上,在法國大革命前後,民間流傳大量有關宮廷和瑪麗皇后 (Marie Antoinette) 低俗的色情文學,正正反映大眾的閱讀品味,可見一斑。流風所及,甚至有人認為這些在地下廣傳的粗俗讀物,對於煽動民眾對皇室和帝制的不滿,其效果大大超乎偉大的啟蒙運動思想。

《撒旦狂筆》提供給觀眾一個吊詭的現象,就是社會和政治越發壓抑,越是能激發藝術家的創作慾望。對於長期失去自由的蕯德來說,查朗頓精神病院為他的繆斯女神提供了一個最舒適的避風港,除了吃飯,侯爵可以沒完沒了地寫作。如果侯爵本身是精神錯亂的話,羽毛筆就成為他最後一根救命草,使他可以從瘋狂中解脫出來。即使幽禁在精神病院,也無法阻止侯爵的思如泉湧,奮力直書。古米亞神父沒收了他的紙和筆,他於是用晚餐紅酒將自己的故事寫在床單上。神父最後將他的牢房清洗得空蕩蕩的,沒有筆,沒有紙,沒有紅酒,床單都給脫了,侯爵於是用切肉刀刺破了指尖,以血書直筆,以塗鴉自滿。當侯爵絲方吐盡,他想到將故事耳語給鄰倉的囚人,口耳相傳,思想因此可以穿越銅牆鐵壁,最後瑪黛蓮在洗衣房接收故事,寫在紙上。
《撒旦狂筆》共分兩幕,各佔超過一小時多的演出。 第一幕圍繞藝術與道德的爭辯,以及薩德設法衝破重重牢房中的障礙,堅持他的寫作。第二幕開始急轉直下,充斥着虐殺與暴力的震撼,氣氛肅殺。在第一幕結束前觀眾聽見一聲女子慘叫,原來其中一個精神病人受到薩德的口述故事刺激,瑪黛蓮遭到暴虐致死。此刻觀眾不期然會問,文字會否成為助長暴力的異端邪說?作家是否要為他作品的影響力而負責?薩德是教壞人還不過是激起本來潛伏在人心的魔鬼?有如侯爵所言:「我的天使!地獄本身就是我鍛造技藝的熔爐」。
在第二幕中,精神病院主管高勒德醫生 (Collard) 一直再誘使神父對侯爵施行酷刑,先切去其手腳,然後斬首式奪其性命,以為這樣就可以終結以後薩德對後世的思想傳播。事實上,薩德在1814年於查朗頓精神病院離世,其遺體被火化,頭顱骨被拿去研究,而據說侯爵在死前仍然無悔於一直以來的創作。此虛構的結局,顯然是要加強國家機器體制的暴力施加於手無寸鐵的文人的戲劇效果,薩德彷彿成為一個為自由思想而犧牲的殉道者角色。而神父在成魔之路上,對薩德一步步殺得性起,變成邪惡的真身。觀眾或想問,人可以以神、革命、或理想的名義去殺人嗎?

薩德一生孜孜的搬演着身體與舞臺的互動,身在獄牢禁室的漫長歲月中,據說他還能夠排演自己創作的戲劇,衝擊性愛與身體的道德紅線,來宣洩他長年抑壓在心底中對自由的渴望。此戲劇要給觀眾的一個重要的訊息,是作者可以被殺死,但思想不可以;苛政可以斷絕一個人的生計,甚至生命,但始終無法控制人的思想。
當現代人將薩德視為自由精神的先驅者,無視於其作品中的猥褻、犬儒精神、及墮落世界,可能是矯枉過正,但亦反映出現代社會對思想言論的受到操控的恐懼和惴惴不安。《索多瑪120天》是薩德在巴士的監獄偷偷寫成,還來不及偷運出來,直至20世紀初才被人重新發現。1956年法國政府想以猥褻罪名 (Offence of Obscenity) 起訴當時出版薩德作品的書商,當時法國哲學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大膽為薩德辯論,促請法國國家圖書館將其作品在禁書列中剔除出來。順帶一提,1960年英國法庭裁定企鵝出版社可以合法發售勞倫斯 (D H Lawrence) 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英國讀者自此才得以閱讀這本小說。
正如胡導演的有所感觸,他最喜歡劇中的一句台詞,他自己翻譯為「面對最困難的逆境,藝術家先至最精神」。(In conditions of adversity, the artist thrives)。當大家身處逆境的時候,藝術家最是精神抖擻,這是因為藝術家具有免疫能力,還是他們本身就是瘋狂的一群?好的舞臺藝術,其精彩之處在於其開放性,它需要觀眾來完成一個演出和劇作。此劇不但可以觸動觀眾的感官,還可以帶給大家在思想上的衝擊,從而重新來審視我們現身處的社會環境。

相片來源:一條褲製作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