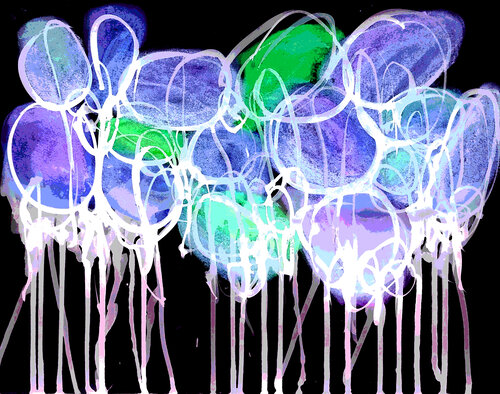香港天籟敦煌樂團近年於本地藝術文化界迅速冒起,成員不乏演藝學院中樂系畢業生。自樂團成立以來,筆者心裏一直存在一個迷思:他們演奏的是甚麼類型∕怎樣的音樂?上月(2023 年 3 月 19 日下午 3 時正),香港天籟敦煌樂團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賽馬會演講廳舉行了《音樂說:中國藝術之美》音樂會。此節目屬於「香港故宮演藝節目」,當日由樂團藝術總監及駐團作曲家甘聖希作説書人,在樂曲之間進行講解;八位樂團成員演奏樂團原創曲目及改編的敦煌古譜,以音樂向觀眾解構東方美學及其各方面的特色。

美學與音樂
音樂會題為《音樂說:中國藝術之美》。説書人甘聖希在音樂會之初,已經向觀眾説明是次活動將會以音樂解構中國藝術的「四美」,當中包括「動感」、「結構」、「情感」以及「氣韻」。音樂會因應以上「四美」分為四部分,並演奏相應樂曲,最後以《青花十二月》(世界首演)作結。
動感
音樂會先以首個介紹的中國藝術美學──「動感」切入,並以「凡有動皆為感」作註釋,簡報亦展示了徐悲鴻《騁馬圖》及敦煌壁畫《牛耕圖》加以説明。甘聖希指出以上兩圖雖然為平面畫作,但其肢體的展示給予觀眾具有動感的感覺。他進一步解説,在音樂欣賞的情況亦然:聽眾可以透過音樂的旋律及節奏,加入想像,從而感受到音樂中的動感。隨後,我們欣賞到樂團兩首原創作品,分別是由朱啟揚作曲的《馬》,以及由甘聖希作曲的《麒麟》。以上兩首作品都屬於容易「入口」的曲目,《馬》是二重奏作品,以笛子主奏,響木(wood-block) 伴奏,配以後十六分音符模仿馬蹄聲,貫穿全曲,此乃十分典型以「馬」為題之音樂創作手法,容易引起觀眾共鳴。《麒麟》則帶有淡淡西域風格,以琵琶主奏,並以中東手鼓(riq)伴奏。甘聖希指出,他想像「麒麟」的行動難以估計,時快時緩的,所以在樂曲中的拍子也作相關的處理。此曲雖為現代作品,但屬於容易讓觀眾接受的類型,同時帶有新鮮感。

結構
第二個介紹的中國藝術美學為「結構」,配以「形每萬變,神守唯一」作註釋(作者按:應為「形每萬變,神為守一」),簡報展示了著名的榆林窟南壁《觀無量壽經變》壁畫。此壁畫以極樂世界為主體部分,展示了殿堂及各種建築物,殿前有八名樂師演奏各種樂器。甘聖希以此壁畫為例,希望觀眾將焦點放在建築物的結構上。他介紹到中國建築一個重要工藝──「榫卯」:所謂 「榫卯」,分別指「榫頭」及「卯眼」,凸出部分稱為「榫」、凹入部分為「卯」;是傳統木工中,接合兩個以上的構件方式。他指出,「榫卯」雖然為建築中的一個小部件,但其作用不能藐視:多個「榫卯」結合一起可以作為古代建築的重要結構,而屋頂上的斗拱,都是以多個「榫卯」結合而成。他以此作為樂曲靈感,寫出了《樹與斗拱》一曲,以笙及笛子演奏。此曲的兩件樂器都各自有固定的旋律動機(motive),其旋律動機會隨着音樂推進而逐漸發展及變化,以複調音樂織體(polyphonic)進行。本來兩個獨立的旋律動機在樂曲開端時離時合,在各自再變化後又再交疊互纏,把「樹與斗拱」在壁畫上的形態以音樂動態化。
情感
接着介紹的中國藝術美學為「情感」,配以「由物生情,由情生象」作註解。甘聖希生動地講解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 1900 年被發現的事件,並藉着此事件帶出在藏經洞所發現的古籍,當中包括不少經文,以及在經文背後的二十五首手抄琵琶譜。接着演奏的《長沙女引》正是在藏經洞發現的二十五首手抄琵琶譜其中之一。根據樂團資料,此曲講述在唐代憲宗元和年間,姑蘇太守韋應物之女曾流落長沙淪為柘枝妓。此曲猶如柘枝妓的內心獨白,訴說了當中的傷感,無奈及辛酸。音樂會所演奏之版本由樂團駐團作曲家朱啟揚根據古譜,以「古譜入音,古曲新詮」方式重新編寫:透過重新思考壁畫,曲名背景,故事等種種留下的痕跡,再加上作曲家自行理解,從而進行全新的創作。甘聖希在現場解説此曲時,未能準確解釋曲名由來,我希望在此補充説明:據中國曲詞學家任中敏考證:《長沙女引》即《柘枝引》。《柘枝引》為曲名,其詞為「柘枝詞」,因講述韋應物之女流落長沙為柘枝妓,於是更名為《長沙女引》以歌唱其人。而所謂「引」,則為琴曲四大曲式之一。宋代郭茂倩在《樂府詩集 · 琴曲歌辭》中引述到:「《琴論》曰: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即是引說其名,用以抒發自己的志向。音樂上,更多為舒緩悠長之曲。樂團資料亦指出,此曲的創作過程中,作品家參考了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的敦煌琵琶譜譯本,重新編為以笙(帶有擴音管之三十六簧笙)、以及兩部中阮合奏之三重奏版本。以笙為主奏,兩部中阮以伴奏形式烘托笙所演奏的旋律進行。但筆者略嫌笙在演奏時音量過大,擴音管亦發出「吱吱」聲,笙的音量蓋過了兩部中阮演奏。在欣賞此曲時突然忽發其想:如果此曲源於古譜,是否可以嘗試使用唐代笙演奏?(當然在音域及技巧上會有一定限制)。但我相信樂團在實驗及創新的同時,使用古樂器能夠更忠實地詮釋古譜。
氣韻
最後一部分所介紹的中國藝術美學為「氣韻」,配以「融景於形,融情於性」 作註解,樂團成員接着演奏兩首樂團原創作品《觸塵》及《洞景》,以上兩首作品皆由朱啟揚作曲,都是啟發自敦煌石窟中的壁畫。甘聖希亦與在場觀眾分享他參觀石窟時,從極為炎熱的室外進入石窟時,由於內外存有溫差,身體會馬上感受到一片清涼。同時,眼睛切換到暗淡光線的石窟內,也需要幾十秒適應。適應過後,張開眼睛便會看到石窟中的壁畫,加上不同的體感溫度,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觸塵》及《洞景》均以現代作曲手法創作:作曲家嘗試以音樂帶領觀眾想像石窟中另類的感官體驗。最後一首作品為《青花十二月》(世界首演),作曲家甘聖希指此新作啟發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館藏「青花十二月花卉紋詩句杯」,描寫杯上代表十二個月的花卉,音樂層層遞進,一氣呵成,但驚喜不大,未有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音樂與敦煌的感應
本場音樂會可以説是以中國美學欣賞切入,引出對應之音樂作品。而這些音樂作品都是樂團的原創作品,皆啟發自樂團主題──「敦煌」。從駐團作曲家對敦煌的探索,啟發出一系列樂團原創作品,以至樂團中各個年青樂手以演奏表達各人對作品的理解及感受。而事實上,整個音樂創作過程,以至藝術創作,都是經歷「探索、啟發、表達」的過程,從中亦會昇華至一個個「循環」,整個藝術創作的過程,其實都是源於感應。所謂「感應」,是一種雙向的思維活動──「有所感,才有所應」。感者屬於主觀一方,即「我」,亦是施動者。應者屬於客觀一方。在此可以對應音樂會開初介紹「動感」時的註釋:「凡有動皆為感」,此句源自《周易.咸卦》,全句原為「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動」指動作,在上例可以類比為樂團成員動身前往敦煌考察;「感」指感應,可以類比為樂團成員在敦煌考察中得到啟發;「應」指回應,得到啟發後的創作是回應的一種;「所應復為感」,可以類比為得到啟發後的創作交給樂師演奏時,他們對音樂各有感受;「感復有應」:樂師再以音樂演奏作出回應,傳遞予觀眾,藝術就是以這樣的形式流動。

在完場時,聽到觀眾熱烈地討論:「這個究竟是中樂?抑或是敦煌音樂?但更像是新音樂?」聽完音樂會後,似乎可以在甘聖希早前的訪問找到答案。筆者認為本場音樂會之作品與他的創作論的第二個層面──「音樂盛載靈魂」相當吻合。甘聖希指:「這裏並不是指不滅的物質。試想像一下,某些音樂響起,你彷彿感受到背後有一種東西。音樂在這刻不只是一堆音符的排列,而是代表一種精神,有人的痕跡在其中。」(https://bit.ly/3nXqxTb)可能對樂團而言,中國樂器只是媒介,敦煌是創意啟發之地,新音樂為創作模式:只是音樂的表達手法和工具,但更重要是當中三種音樂形式之間的互相感應──從意念到創造;由有形到無形。
相片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