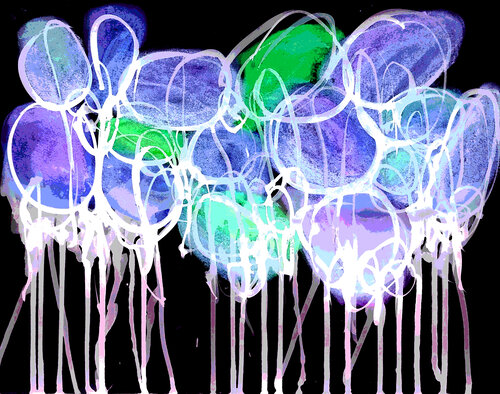訪問場地提供:JIKKA
香港電影於去年中開始出現小陽春,多部電影叫好叫座,熱潮到今年初方興未艾,《毒舌大狀》大有打破歷來票房紀錄之勢;該片和《給19歲的我》、《1人婚禮》同樣有不少好評。對於這個熱潮,近期巨作《正義迴廊》的監製翁子光分析,一切是數個契機的結合:「碰巧戲院因疫情關閉了幾個月後重開,大家又不能去旅行,於是有很強進入戲院消費的意欲;同時疫情和社會運動又令香港出現很多變遷,創作人和觀眾都累積了很多感受,創作人藉電影表達了出來,觀眾從中找到了歸屬感。這批電影拍攝到觀眾關心的內容,出現情感主導的狀況,與觀眾有強烈的互相分享和交流。另外,個別電影受歡迎也會帶動觀眾去看其他電影,就像打開了缺口。」
與最近幾年冒現的多名新導演相比,翁子光加入電影業已逾20年,可算是中生代的導演,經驗較豐,成績早已獲得認可:他執導的《踏血尋梅》(2015)在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橫掃7個獎項;新作《風再起時》也是香港影迷引頸以待的電影。他在電影生涯和經驗,可以為香港電影業看似復甦後應何去何從帶來啟示。

翁子光自小喜歡看電影,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看優先場,坐在電影院第一行,感受到觀眾反應非常熱烈,開始為電影著迷。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最能打動他:「那個酋長角色將整個洗手盆拔起,擲破牆壁,然後走出去的一幕,令我流淚。我開始意識到電影可以結構性地表達人類的生存環境和一些微妙的東西,是一份完全的體驗(total experience),於是我很想參與電影工作。」
他加入電影圈的機緣,來自念中七時在社區中心得悉一家電影公司招募年輕人在職培訓。雖然只是做小工,也沒有正式薪酬,僅得車馬費,但他還是做得很開心。結果他連高級程度會考有些科目也沒有應考,放棄了進大學修讀電影的念頭,直接就入了行。
當時是1998年,正值香港電影市道最差的時候。翁子光說:「行內很多人意興闌珊,流失率高,所以新人入行也不困難,但是要不計較薪酬,也願意捱苦。我志在學習,接工作從不討價還價,很低的條件都肯做。那時候真的很貧窮,有時要跟家人借錢,也曾經將拍戲用作道具的漢堡包帶回家,吃了一個星期。」雖然家人有傳統想法,期望他找比較穩定的工作,但他決定從事電影業,他們也沒有反對。
翁子光入行時已矢志要成為導演,因此不久後他修讀了香港電影導演會1999年 的編導培訓班。但是他的電影生涯跌跌碰碰,也不容他刻意經營。翁子光做過多個不同崗位和部門,首先是音響效果,其後又做過編劇、場記、副導演、美術部和製片組,總之那裡有空缺,他就去做。他說:「這種經歷對我後來做導演和監製有幫助,因為各個部門的工作我都有基本了解──很少人的經驗是橫跨這麼多部門的。而且,在最不景氣的時代工作過,練就了效率,也建立起一種精神:無論環境多麼惡劣、資源多麼匱乏,都能夠拍戲,這可能是我和新一代導演有點不同的地方。」

那個時期,翁子光除了電影外,還做過很多其他工作,包括拍攝香港電台的電視劇、紀錄片、廣告和企業宣傳片、主持網台節目、寫影評等。他不諱言,這些都是基於「有工作就做」的心態接下來的。不過現在回顧,這些經驗同樣有助自己後來執導電影:「我有機會正式擔任導演,雖然好像在拍很商業化的東西,但其實是一種練習。」
入行約9年,到2007年終於得到首執電影導演筒的機會,拍攝《明媚時光》(2009年上映),既是翁子光長期努力累積的成果,也是機緣巧合。當時他為一家電視台做訪問節目,結識了一位擅長拍社會寫實題材的導演,建議對方拍攝自己構思了的一個故事,不過計劃後來告吹。有一次他跟亦師亦友的許鞍華談起這個劇本,許建議他不如自己執導。結果他找到一位朋友張雯願意出資約100萬元,另外還有一些工作人員義務幫忙,拍成了《明》片,以一名青少年的成長故事來側寫香港回歸10年的改變,當中也牽涉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制度和文化碰撞。雖然該片在香港的票房僅得約4萬元,但是影評人的口碑不俗,也獲得多個國際電影節的青睞,邀請參展;翁子光更憑這部電影取得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項的提名。
他承認,《明》片的成績令自己獲得認可,爭取到更多執導機會:「我相信業內人士從這部電影看到我有魄力,用這麼少資金,可以拍到這麼多場景,動用這麼多演員,是有製作價值的。他們覺得可以試試給這個小夥子多一點資源去拍戲。」他指當時新導演不多,所以獲得很多洽談開拍新片的機會。
那時候翁子光已在構思拍攝發生於2008年的少女王嘉梅肢解案,即《踏血尋梅》,劇本贏得了香港國際電影節屬下「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的獎項,也正與一家公司商討拍攝計劃。當時他仍是新人,公司對他雖有信任,但卻提出很多要求和控制,令他很不習慣:「從戲名、選角、劇本內容、製作預算到整部戲的包裝,雙方都不斷爭議,結果計劃胎死腹中。」(註:其後拍成的《踏》片是另一家公司的投資。)
翁子光說找不到資金開拍《踏》片,導致他有一點抑鬱。就在那個時候,一名監製有幾個故事意念,找他當導演拍攝。翁子光覺得可算是新版《靚妹仔》(1982)的《微交少女》(2013)的題材很吸引:「這種描述殘酷青春的故事很適合我,而且我也喜歡用新演員,我相信可以拍到很紀實和有活力的味道。」
不過事與願違,翁子光與這名監製在製作意念上有很大分歧,合作並不愉快,《微》片的成績也遠不是他預期的。但在這次經驗中他也有得著:「我更為珍惜在獨立自主的情況下拍電影,不要人家叫你拍甚麼,你就拍甚麼。有一些底線不可以模糊──《踏》片融資失敗令我沒有了底線。後來我會分析事情輕重,跟老闆合作就像跳舞,有時他進一步,我退一步,有時我進一步,他退一步,你要找到方法跟他周旋。」

這次經驗也促使翁子光決心再找資金拍《踏》片,由於已獲得郭富城未經商討片酬已答允接拍,演員陣容有了保證,找投資者變得較為容易。他說:「結果拍出來還是文藝片,當時我沒有考慮商業問題,只是盡情發揮。有人批評我的電影好像是拍給影評人看的,我覺得也沒有說錯,我喜歡自己的作品可以供人分析、思考,因此會拍出像《踏》片的電影。」
雖然翁子光也預期這部電影會得到正面反應,但是評價還是令他喜出望外,他分析:「吸收了前兩部電影的經驗,一部太自由,一部太不自由,這一部可說找到了平衡點;另外我也特別重視選角,找能夠呈現質感的素人演出——雖然白只和春夏也有電影以外的演出經驗。」
《踏》片成功後,翁子光的監製期望他可以更上一層樓,開始洽談拍攝內地合拍片。即使不少香港影迷對合拍片頗有非議,一直拍純本地製作的翁子光說,轉攻合拍片的過程中也沒有很多顧慮:「如果要將製作規模擴大,就一定要拍合拍片。」

在拍攝以內地一宗真實事件改編故事的計劃告吹後,翁子光就想到自己多年前寫好、以上世紀50年代的「四大探長」為題材的劇本。他解釋為甚麼會想拍這段在他出生以前的歷史(內容中也加插很多浪漫的虛構情節):「我小時候看電影,看過呂樂和藍剛的故事,已經想像由自己來拍會是怎樣的,這就像童年夢想;而且合拍片可以在內地搭建貌似50和60年代香港的佈景。我其實是在用合拍片的資源,來拍一部屬於香港的電影,借助這兩個人物來重塑昔日的香港。片中有很多符碼(code)是香港人才可以解釋的,內裡的香港情懷也只有香港人才會有深刻感受。那是已經消逝的時代,我希望引發香港人對那個時代的念想。」
從2007年開拍《明》片至今約16年,翁子光只拍了4部電影(另有一部已完成拍攝,正在剪接),他坦言這數量不理想:「我不會諉過於近年的社會形勢、新冠疫情和合拍片制度的變化,但這些確是原因,令我要重新摸索作為導演,自己的定位是甚麼;另外當然也要面對內地的審查。以往自己較為被動,遇上問題就會逃避,寧願將時間用於創作。今年開始我會更為積極,也會同時兼顧多項工作。好些我喜歡的導演,像杜琪峰,拍了很多電影,正是因此不斷有新的意念,我希望也可以這樣,因為不論對於自己的電影路或香港市場,我都看到自己要做甚麼。」他其中一個目標,是自己的製作能令從業員(特別是新人)感到「好玩」:「雖然在捱,但會覺得好玩,能給你希望,而不是辛苦過後徒勞無功,我覺得要為行業營造這樣的氣氛。」

面對最近的小陽春,翁子光表示:「打開了缺口,我們要保持警覺性,持之以恒,不能像過去那樣跟風濫拍,胡亂拍《飯戲攻心2》或《正義迴廊2》,這樣就會令觀眾失去信任。」他認為,新一代導演雖然表現出色,但還需要進一步的突破:「他們不是用類型片來吸引觀眾──類型片的觀眾消費模式比較簡單;現在作為賣點的往往是個別議題或演員的表現。導演著重表達自己喜歡的內容或情懷,但缺少了跟市場溝通的想法。」翁子光相信,這一代導演要有上世紀70年代末冒起的「新浪潮」導演那股銳氣和探索精神,港產片才可能真正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