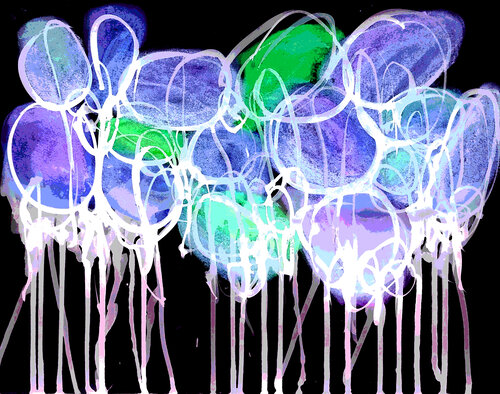過去10年,香港電影市道疲弱,反而更多有心人為「言志」而拍電影,著重帶出訊息或分析社會問題。露宿者、精神病患者、失明人士、少數族裔、外傭、清潔工人等弱勢社群近年都成為了電影題材。到今年11月,香港再有兩部「社會問題電影」上映,分別是《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記》,均是由爾冬陞監製。
香港電影其實早已有「關心社會」的傳統。在上世紀50、60年代很多展現人文關懷的粵語片中,貧窮都是極為常見的戲劇元素,劇中人物面對的困難(戲劇衝突)往往皆因貧窮而起。但是當時的作品對貧窮問題成因的理解通常仍停留於個人層面,可能是主人翁暫時運氣不濟,頂多是土豪劣紳為富不仁,而極少歸咎於制度或政策。因此,這些電影提出的解決方法,大多也只是強調小市民守望相助或富商覺悟前非等。

說到香港社會問題電影的高峰,肯定要數龍剛在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期執導的幾部叫好叫座的作品:《英雄本色》(釋囚,1967年)、《窗》(失明人士,1968年)、《飛女正傳》(邊緣青少年,1969年)和《應召女郎》(性工作者,1973年)。龍剛對這些作品探討的問題態度極為認真,甚至有頗強說教意味,例如在《英》片中很詳細地介紹了釋囚協會工作,以及《飛》片末段花了幾分鐘,讓曾江飾演的女童院院長徹底分析青少年問題的成因。
到了港產片的黃金時代(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大部分製作商業掛帥,社會問題電影不多(假若不包括以性工作者或邊緣青少年為題材的電影),往往都是以個別弱勢人士為主人翁,如《何必有我?》(弱智人士,1985年)、《聽不到的說話》(聽障人士,1986年)、《癲佬正傳》(精神病患者,1986年)和《籠民》(籠屋居民,1992年)等,大多會作較為戲劇化的處理,甚或用煽情的橋段,以通常悲慘的故事來吸引和感動觀眾,很少會用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導致這些現象的問題根源。近年的作品偏好用比較冷靜抽離的風格,極少煽情內容,但是同樣會以弱勢主人翁的故事為主。從這角度看,《白》片其實跟過去的社會問題電影頗為不同。
電影以真實的新聞事件改編,講述一家長者和殘疾人士院舍虐待院友,記者調查和報道事件之餘,更揭發院長涉嫌性侵院中的弱智女子。這種真實事件要拍得精采,很可能比虛構的故事更為困難,因為事件的情節大眾記憶猶新,故事發展不會有懸疑味道,加上事件的受害者是弱勢社群,不容創作者添加過分煽情的枝節,否則會有剝削之嫌。《白》片未正式公映已獲得大量好評,端賴導演說故事和人物設計的功力。
電影以平實的方式敘事,勝在細節豐富,令觀眾對事件和背景有充分了解。同時片中有逾10個人物都呈現鮮明的特色,加上絕大部分演員演繹得恰到好處,因此即使觀眾早已知道故事結局,還是會給劇情觸動。電影在臺灣金馬獎已獲得5項提名,包括余香凝、林保怡和梁雍婷獲得演員獎項的提名,3人的表現都令人耳目一新,但另外如胡楓、姜大衛、鮑起靜、陳湛文和周漢寧等的演出,也足以問鼎演員獎項。

《白》片其實用上比較傳統的手法,平實中不避間中作較戲劇化的處理(特別是院舍長者露天洗澡、女記者在辦公室走過燈光逐漸熄滅等場面)。近年不少港產小品(並不局限於社會問題電影)往往喜歡刻意削減「戲味」,例如不按時序,將各場次的先後次序互相穿插,或刪削理應交代的情節(但又未見有特別原因或效果要這樣做)。《白》片的處理更為「大路」,既能營造戲劇張力,也不會予人煽情之感。
與大部分社會問題片相比,《白》片的特色在於沒有只從弱勢人士的角度出發,也較宏觀地指出了導致這宗悲劇的癥結──並非單純某些人的過錯,而是制度上用於安老和殘疾人士服務的資源不足。而由於電影的主要視點來自揭發事件的記者,因此《白》片更多了另一個面向,就是探討新聞工作的價值和前途(女主角問:「10年之後,仲會唔會有記者?」)。更進一步,電影還詰問我們面對不公義時,能否做到甚麼改變世界。這些處理令電影的眼界和視野更提升了一個層次。
筆者以前從事新聞工作,認為片中有關採訪的情節和行內人物的描寫既有相當寫實的筆觸,也有不足之處。精采的是主角余香凝給年輕同事問及工作理想時,顧左右而言他,到院舍的新聞刊登後,大獲好評,她接受眾同事祝賀時淡然處之,這些描寫均顯示出不少資深新聞工作者雖熱愛工作,但卻不會將這份熱情或抱負隨便表露或宣之於口,反而會用看似犬儒的姿態掩飾(不斷表示擔心職位遭裁撤)。但另一方面,她進入院舍偵查的過程卻或許過分輕易和順利;與上司就採訪內容產生的衝突也顯得表面化;作為資深記者,她要從議員和大律師口中得到一些相當淺易的資料和解釋,又未免不甚合理(當然,這鋪排很可能是為了方便內容表達)。
反觀《年》片對社會問題卻用了截然不同的切入方法。宣傳文字指電影針對的是青少年自殺問題,但是導演真正聚焦的,其實是男主角(盧鎮業飾)的成長故事,只是其中前後牽涉兩宗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而已。情節和人物都寫得細膩動人,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佈局,令觀眾到中段才恍然大悟。
筆者最欣賞的處理,是電影描寫任職中學教師的男主角相當關心愛護學生,但其實跟學生的相處還是有很多自以為是的盲點。以青少年為題材的電影,容易出現一種成年人(創作者)高姿態的「關愛」,並以此作為青少年問題的答案:以為自己充分了解青少年,可以憑能力、資源和關心,協助下一代完全解決他們面對的困境。《年》片沒有這個弊病,導演頭腦冷靜,將教師、社工與學生的關係描繪至大致上平起平坐,學生還是要自己處理問題──但是教師願意幫忙。

反過來看,電影剖析青少年自殺問題不算深刻。自殺的少年面對的種種困擾和痛苦都可說是源於父母給予的壓力(又以父親為主),而盛年時期的父親角色(鄭中基飾)的性格塑造又稍嫌單向平板,反而不及片中其他細節那麼細緻立體。因此,《年》片其實是略帶悲情的成長小品,更多於是社會問題電影。
電影畢竟並非學術論文或政策報告,未必需要對社會問題提供深入的分析或解決方案,能讓觀眾關心和初步認識問題已經足夠。至於電影能否藉著探討問題而「改變世界」,更是難有答案。不過,《白》片中院友姜大衛的對白「唔好為做啱一件事而內疚」,以至兩位導演願意排除萬難,拍攝這種票房不易討好的作品,或許已為答案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