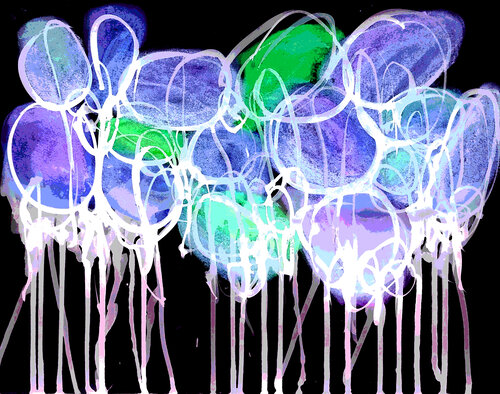飲江和我相識已經二十多年了,討論過的大大小小課題實在太多,都沒有筆錄下來,這次算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們的訪談以回顧生平為主,也旁及中英對照的《Moving a Stone: Selected Poems of Yam Gong搬石:飲江詩選》(James Shea與謝曉虹合譯)。關於飲江作品的訪談,王良和的〈逆反連扣,別有蒼涼——與飲江談他的詩〉(收於《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以及鄭念太的〈太極筆法:時空的探索—— 專訪飲江〉(刊於《聲韻詩刊》第五十四、五十五期合刊),十分詳細,這篇訪談文章可算是一點補充和概覽。

回顧生平
飲江創作超過半個世紀,從七十年代開始發表新詩,一切由《伴侶》半月刊開始,《伴侶》是左派的文藝雜誌,主要面向青年和學生,詩歌方面的編輯者是舒樺(李怡)和陶融(何達)。
飲江形容六、七十年代文藝界的大環境是「從激越到消散」,六十年代是火紅年代,人們走出個人的圈子,熱切思考世界大事,為了更合理的社會,設想準則及原則,甚至想改造世界。到了七十年代,飲江投入創作,早期作品相當昂揚熱情,也引來溫健騮以筆名林原發表文章〈飲江的詩〉(刊於《盤古》第七十一期,1974年7月1日),文首即形容道:「飲江的詩,豪邁、剛健,洋溢著對生命的熱愛,對美好世界、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時,字裡行間也充滿了戰鬥的誓言。」
飲江回憶說,在七十年代後期接觸到生活化的香港詩歌,這些作品自然、樸素而且真摰,也不要過去的格套,除此之外,飲江也閱讀到Jean-Maire Schiff和新加坡藝術家陳瑞獻合譯的《雅克・卜列維詩選》(1970),法國詩人卜列維(Jacques Prévert,又譯普雷維爾)的詩,充滿幽默和趣味,運用戲劇性的手法,不著跡地帶出個人關懷,卜列維以及耶麥(Francis Jammes)、艾呂雅(Paul Eluard)等法國詩人的作品,吸引和影響了飲江。
閱讀是飲江最重要的興趣,他的生活離不開書籍,多年來買了許多書。飲江自言對藝術、社會和生活感好奇,但沒有周遊列國,就是藉著看一本又一本書,了解他人的故事。
在七十年代後期,飲江一度停止發表新作,八十年代是飲江在創作上的重要時期,但他說其實自己沒有甚麼朋友,也難有朋友,親戚不看他的詩,他自己也不在任何文學圈子內。事實上,飲江獲得過職青文學奬、工人文學奬、青年文學奬及香港中文文學奬,詩作頗受人肯定。〈廣告人〉、〈邊緣人〉、〈新填地〉、〈美人魚〉、〈靜夜思——寄父親〉、〈家常〉、〈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遇合〉、〈飛蟻臨水〉等等都是八十年代的作品,飲江更在1986年,和朋友吳美筠、洛楓、林夕一起創辦了詩刊《九分壹》。
〈飛蟻臨水〉是飲江的代表作,原刊於《突破》,余光中在〈一枝紫荊伸向新世紀──為「第二屆香港文學節」而作〉一文就讚許飲江的詩〈飛蟻臨水〉:「把尋常人家在風雨前夕佈置孤燈盆水、溺殺飛蟻的景象,寫得神奇而幻美,偏偏語言又如此單純、乾淨,真是一篇傑作。」(收於《藍墨水的下游》)
作品不斷累積,飲江在1997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更榮獲第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奬。飲江指,當時呼吸詩社出版《呼吸詩刊》,自己投稿,認識了一些朋友,自己的詩作已足夠成書,就順理成章出版詩集。飲江補充道,九十年代中期之前,詩壇一度比較沉寂,但隨著王良和在香港藝術中心開辦詩作坊,零點詩社、呼吸詩社、我們詩社、吐露詩社,以至各大學詩社出現,而且《詩潮》在2001年創刊,葉輝、關夢南、崑南等大力推動,於是詩壇活躍,網絡上和紙本上都熱鬧起來。
飲江的詩作不斷累積,2010年出版《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2022年再出版《於是搬石伏匿匿躲貓貓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三本詩集的內容互有重疊,書題也是在舊基礎上加入新字眼。


英譯詩集
2022年對飲江而言是比較重要的一年,他出版了兩本書,包括中英對照的《搬石:飲江詩選》。在「香港文學生活館」創會的晚上,飲江遇到 James Shea和謝曉虹。他們在翻譯飲江的詩,既關心香港詩歌也希望多向世界介紹。飲江聽到自然歡喜,只怕是煩勞他們兩人。
之後,從2016年或更早,大約費時六、七年吧,James Shea和謝曉虹悉力翻譯,約莫便翻譯了上百首了。對飲江而言直是從不敢想天上掉下來一大禮物。但這更是一大工程,畢竟翻譯本身有一定要求,何况是詩歌。既要了解文本脈絡,以致文化上種種關涉,更是交流對話過程的不盡發現和發見。
飲江又說,自己的詩牽涉了本土以及過去的人和事,翻譯又涉及詞彙、語句、語法等等的技藝,飲江欣賞兩位譯者用心翻譯,而且寫了大量的注釋和箋注。
《搬石:飲江詩選》共收四十三首飲江詩作及英譯,選出一些值得細味的作品,例如〈新填地〉,這首詩原刊於1983年12月7日的《星島晚報‧大會堂》(劉以鬯主編),寫的是上環新填地(今信德中心及港澳碼頭一帶),詩中牽涉了飲江少年以來的許多回憶,包括了各色人等、賣藝者和勞苦大眾,如穿斑衣的簫王、生鬼七、吞大石卵外江佬、行船仔、白鶴老叟、花旦、說書人、照田雞阿二、鬼谷神算、塘西蘇小小、茅山師傅等等,最後只剩得一個海邊的企街姑姑,見盡歲月生涯。
〈新填地〉不容易翻譯,因為當中有許多人物,以至昔日的文化和事物,飲江在詩中寫了「行船仔買金烏蠅」,他指這金烏蠅原來是西班牙烏蠅,是一種春藥,最終翻譯是Spanish fly,而不是直譯為Golden fly。
又例如另一首〈把豉汁抹在䱽魚的身上〉,這是一首對話體的詩作,人與魚之間來回對答,大概是圍繞著食、色與死亡。最後,人如是說:
「是的
當魚說話
人應該沉默
讓我把鼓汁
加些許蒙汗藥
輕柔地抹在你的
我的身上」
飲江認為蒙汗藥所指可能有些含含糊糊,蒙汗藥大概是迷藥、春藥之類,最終蒙汗藥翻譯成love potion,可見兩位譯者的選取和研究工夫。
《搬石:飲江詩選》的內容很大部分也因應外國讀者而揀選,都是兩位譯者的選擇。飲江說他自己便是受惠者、受益人,透過這本書,他更加認識自己,原來是可以更好的自己。飲江認為翻譯是妥協,是協調,是創造,是轉化,也是相互理解和相互受用的遭遇方式。當中牽涉了語言和言說,更帶來新的視野,乃至新的感受與覺知。



小結
飲江自七十年代開始創作,寫詩超過半個世紀了,他希望透過寫作,讓事情發生,也希望讀者從他的詩作中,找到一點意思。飲江說,自己的詩作中未必有很確實的意義,但希望詩歌能夠引發他人投入其中,詩人和讀者一起補遺,而至於發現新的意味。
最後,飲江引述科學家愛因斯坦的一句話:「努力學習,等待啟示。」他說自己總是不認真地探索,也沒有足夠的條件系統地學習,但多年來一直保持讀書的熱情,希望透過閱讀不斷學習,鑽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