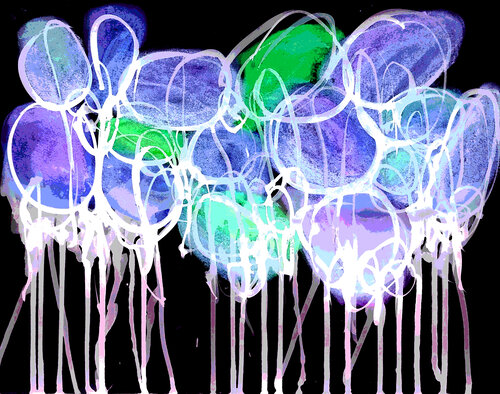今年(2024)1月12日,筆者於香港大會堂劇院欣賞了由香港作曲家聯會主辦的「傳承 . 美樂之河:香港天籟敦煌樂團音樂會」。適逢今年為香港作曲家聯會成立四十周年,聯會以三場「傳承 . 美樂之河」音樂會作誌慶活動,分別與演奏室內樂的Nova Ensemble;以中樂室內樂結構組成的香港天籟敦煌樂團,以及香港兒童合唱團,三種不同類別的音樂機構合辦音樂會,共演出二十多首不同風格的本地作曲家原創作品。每場音樂會中亦會有一首由聯會委約的世界首演作品。今場音樂會為「傳承 . 美樂之河」慶典之第二場音樂會,由香港天籟敦煌樂團演奏七首聯會會員作品,並由樂團駐團作曲家甘聖希擔任指揮。

以往我也曾欣賞過香港天籟敦煌樂團的演出,而當時的節目內容都是樂團自行主理,效果令我十分驚喜。而本場音樂會也算是樂團首次演出非樂團原創作品。音樂會以聯會主席梅廣釗博士作曲的《東風來》(為笙、簫、琵琶、小阮、中阮、箜篌及敲擊而作)打開序幕。根據梅博士於場刋的描述,此作品本來為粵樂五架頭而作,根據此場音樂會而改為民樂八重奏。樂曲以洞簫和古箏的對話開始,旋律自然樸素,中段以其他樂器的加入,以豐富樂曲的織體(texture,即旋律、節奏、和聲等組合的方式),加上速度的推進,把情緒逐漸推到頂點,最後以輕音作結,是一首樸實而富趣味性的作品。接下來演奏的是由陳錦標博士創作的《春暉園》(為笛子、高音笙、古箏、琵琶、中阮及敲擊而作)。此曲早在1998年香港藝術節首演,以即場電子聲效襯托。根據陳錦標博士在場刋所述:此版本以彈撥及敲擊樂器穿插在笛子和笙之間。接下來的是由陸尉俊博士作曲之《彈撥搖滾》,此版本改編自作曲家另一首琵琶獨奏作品《搖滾琵琶——FIGHT!》,而《彈撥搖滾》則為中樂室樂小組版本。樂曲以《十面埋伏》的引子引入,彈撥樂在變奏下加入搖滾節拍,此曲對樂師的技術和整體合作都有一定挑戰性,也推進了音樂會的氣氛。上半場最後一首樂曲為《苦行》,由蘇傳安作曲。此作品為箏、中阮及敲擊而作。作曲家在場刋寫道:樂曲以中國傳統音樂與現代作曲技巧結合,試驗將不同文化揉合。此作品雖然只用了三件樂器,但每個聲部環環緊扣,樂段及起伏亦清楚分明,令我印象尤其深刻。

而下半場則以洪銘健博士作曲之《八陣圖》開始,此曲改編自2013年為中樂大樂隊所寫的版本,改編後由曲笛、高音笙、古箏、琵琶、中阮、大阮及敲擊樂演奏。接着演奏由陳明志教授作曲之《觀自在敦煌》,此曲由香港作曲家聯會委約創作,以祝賀香港作曲家聯會成立四十周年。樂曲並沒有指揮,由舞台上的笛子(兼奏簫)、笙、古箏、琵琶、中阮、大阮及敲擊樂手互相配合演奏,中阮及大阮樂師亦需兼奏以水晶制的頌缽(Crystal Singing bowl)。根據陳明志在音樂會前受傳媒採訪時所述:「此曲取材自敦煌壁畫中的《觀無量壽經》變圖,在音樂創作上,以空間記譜和樂師按樂譜指示內的即興,展現畫中的形象和氣氛,並嘗試以樂師在音樂演奏時的移動來展示空間流動的過程。」最後一首樂曲為《謝謝你的時間》,由香港天籟敦煌樂團駐團作曲家甘聖希作曲及指揮。樂曲為笛子、笙、古箏、琵琶、中阮、大阮及敲擊而創作,亦是樂團經常演奏的曲目之一。
此場音樂會入座觀眾以目測達七成,以劇院合共有463個座位計,即共有近三百名觀眾入場欣賞,此成績的確十分不錯。但我觀察到大約演奏完第三首樂曲後,陸續有觀眾在樂曲完結後離場,幾乎每首樂曲都有這樣的情況。中場休息過後,大堂後座多了不少座位,顯示有部分觀眾選擇在中場休息離場。而在我一直欣賞音樂會時,身後兩位女士幾乎在每首樂曲完結後都交頭接耳地互相討論,內容大概都是:「這首你聽得明(白)嗎?」另一女士會回應:「好高層次㗎,我哋都唔識藝術,再聽聽啦!」她們的對話,把我內心一直的疑惑再次引起,令我再度思考:現代音樂的創作應當如何定位?如何可以在作品的藝術性和受眾品味之間取得平衡?演奏者和作曲家之間,應當如何溝通,使作品更有效詮釋及表達?

一場音樂會,不外乎三個主體的互動:作曲家、演奏者和觀眾。從作曲家的意念到完成樂曲創作;把完成的作品交給演奏者演繹,當中涉及排練、作曲家把其意念與演奏者分享,再由演奏者以自身經驗演繹。就如俄國作家Maxim Gorky所言:An artist is a man who digests his own subjective impressions and knows how to find a general objective meaning in them, and how to express them in a convicting form. (作者譯:藝術家把其主觀感覺消化,從而找到一個客觀的意思,再把它以具説服力的方式表達。)以上每個環節環環緊扣,從作曲家清晰明確的作曲動機而生,有效地轉達予演奏者作傳導,最後由觀眾感受作品的溫度,觀眾的回響鼓勵了作曲家及演奏者。這樣的音樂帶有感染力,也是使音樂生生不息的泉源。但若果其中一環沒有發揮其作用,難免容易陷入混沌之中:如演奏者不明作曲家的意思,以致觀眾不能理解作品的內容,對作品失去欣賞的耐性。
以此場音樂會為例,除了部分作品有明確的旋律外(如《東風來》、《春暉園》、《彈撥搖滾》),其他的作品多以音樂動機(musical motive)作主導,從而運用擴展及變奏等手法發展樂曲,音樂結構亦非以傳統方式構作,所表達的不一定是一段故事,可以是一種感覺,或者營造一種氛圍。 作曲家會在音樂織體的構成,不同樂器的音色混搭,以較不常見的和弦及複合拍子結構花心思。此類作品相比帶有明確旋律,遞進式音樂結構的作品,無疑是對指揮及演奏者的挑戰性,對一般觀眾更甚。作為現場觀眾的我,在部分時間也難免會走神。同樣從事演奏工作的筆者,也感受到台上的演奏者在部分時間只是演奏音符,對樂曲並不熟練,對每段音樂需表達的情感也不太投入,這些都可從他們零落的音符,不連接的樂句中深切地感受到。再補充一點,旋律和織體若果清晰,對於演奏者來說也較容易理解和有較好的演繹,對音樂也有更大修飾和發揮的空間。但若果樂曲涉及非古典及浪漫時期的創作手法,例如運用了polyphonic(複調音樂)的多織體創作,加上脱離調性的音符、複雜的對位手法、非傳統的樂句和弦等,到這個層面,便很需要作曲家與指揮有效協調,指揮從作品及作曲家所提供的線索,抽絲剝繭地反覆試驗,並向樂師清晰地指示其功能及崗位。通過排練不斷實驗,以協調聲部間的合作,這樣才能把整首全新作品從midi(音樂數位介面)中解放,從意念轉化成活生生的音樂,與觀眾對話。

本人作為演奏者,從演藝學院在讀期間至現在也曾演出過不少本地作曲家的新作品,當中不少創作蘊含創新的意念,大膽而且前衛。歷史上,香港本地作曲家的作品往往可以重新定義音樂,並打破中樂的刻板印象。例如有香港新音樂之父之稱的林樂培,他在1970年代所創作的《秋決》及《昆蟲世界》,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不少樂團仍會演奏,亦成為永不過時的一代經典。新音樂的創作無疑是香港中樂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但始終新創作並非傳統耳熟能詳的曲目,不論是作曲家、演奏者、指揮,都必需花更多心思以完善,理解及演繹這些新音樂,方能把音樂中的訊息傳遞予觀眾。最後,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何不先從場刋的文字着手?作曲家不妨加多一點筆墨盡力向觀眾介紹您們的作品,再由舞台上已完全理解您們的作品的演奏者,引領觀眾欣賞您們的創作結晶,從中循循善誘觀眾,使一個個製作能引領他們提升藝術欣賞水平,就像一個互相影響和成長的過程,以達致「觀」「演」(觀眾及演奏者)相長的有機(organic)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