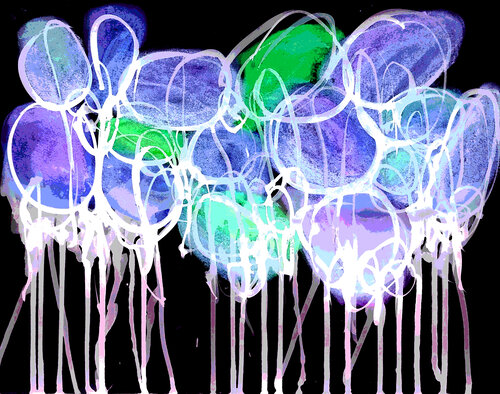作品的英文名稱是 PHONATE,意思指發聲,中文名為《鳴》。(註)讓我好奇的是在場刊上,作品名字中間被劃了一條紅線。若聲音被「劃去」了,我們該如何表達?若不能發出聲音,人與人之間,又如何聯繫?
四位舞者先後出場,各據一方。互相像看不見,彷似沒有關係。但當口琴聲出現,在場中迴響,舞者以動作互相回應,他們之間就產生了連結。舞者嘴巴前貼上薄而小的八孔口琴,聲音就隨著他們的呼吸傳出來。

他們各處一隅,以緩慢而平均的節奏,沿著一個龐大圓圈的軌跡轉動。舞者舞動的路徑及形狀雖各自不同,但讓我注意的是,他們的動作和質地都帶著黏稠感,綿延不絕。這個畫面令我聯想起兩儀圖,一個代表太極概念的符號。兩儀圖中黑白二色「陰陽魚」頭尾緊緊相接,彷彿在圖中緩緩游動,代表著萬物是相互依存並統一的關係,就像舞者們看上去分處各方,表情和動作差異,但本質相同(呼吸、流動、專注……),並以這些共通本質,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形成了圓圈。誠然,我的聯想跟早已知悉 Wayson 一直浸淫於太極鍛練是有一定關係的。
接下來,急促密集的雜音從喇叭傳來,與舞者節奏截然相反。隨後更有低沉的頻率出現,使勁的震動每人的耳膜。當聲量越來越大,穿透整個場地,坐在觀眾席的我,少不了受到干擾,留意到自己的呼吸也跟著有些紛亂。然而,舞者們的節奏並未因此受到影響,動作綿延依然,繼續專注在身體及圓圈的流動中。時間越久,我的心中亦越加欣賞,因為堅持不受外界影響,維持自己的節奏,委實不易。
當他們逐漸向圓心集中,流動亦隨之加快,最後聚為一團,互相穿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看著混沌漸轉化成一直線,舞者手牽着手,開始自我旋轉,速度越來越快,好像快要被甩出去一樣,讓我心弦緊繃。加速至極限一瞬,忽然斷裂!他們一分為四,轉動卻沒有停止,反而擴散開去,如同被狂風吹過的蒲公英,飄至各方。


在蒲公英不斷自轉的時候,剛剛他們聚合又分開的畫面浮現眼前,莫名的既視感,隱約的不安⋯… 下一刻,我想起了。是的,是我們生活中熟悉的離散。是的,呼喚、回應、聚首、團結、分裂,相信大部分人都經歷過,因此能夠共鳴。
然而蒲公英似的舞者一路轉著,轉著,轉著⋯ …還未停下。為什麼不停下?彷彿過了很久,依然在轉。還是未停下。我在問:究竟有什麼驅使一個人不停下?為什麼仍在堅持?
終於,他們疲憊不堪,停在觀眾席前。汗如雨下,她或他扶著膝頭、坐下、站著,口琴傳出微弱的聲音。他們再次散開各方。今次,他們小心翼翼,循著口琴的呼喚,緩步接近,在不遠不近的距離,互相陪伴著。最後,他們再聚。這次,他們以琴聲作媒介,並同步著大家的節奏,達到同呼同吸的境地。


舞者在演出中呈現的堅持讓我觸動,亦對此堅持背後的動機感好奇。表演中出現多次的聚合與離散,以及舞者間的連繫,讓我有所共鳴。於是表演完結之後,找到編舞盤彥燊Wayson,問他怎樣看這兩樣事情。
關於堅持和收穫。原來Wayson有練習跑步;有時候,到達極限那刻會覺得自己跑不下去。但他嘗試堅持下去,突然有一股新力量產生,讓他可以繼續跑落去。他認為堅持總會有些收穫。表演中呈現的堅持令我這觀眾動容及思考,相信對創作團隊及表演者來說,也是一種收穫。
關於聚散與連繫。Wayson分享他的人生經歷過轉變,包括拍拖、結婚、家人的離開等等,讓他留意到生活中的相聚與離散。在排練過程中,他曾帶領舞者玩一個關於距離的遊戲,要表達關心,但不可以侵佔對方的私人空間。在演出裡,舞者以口琴聲、呼吸及動作為媒介,在口被封住,無法說話的限制下,呼喚及回應他人,同步頻率,建立連繫,讓我看到人與人超越距離和語言,互相連結的可能和期盼。
另外,關於作品名字的藝術設計,Wayson說,靈感來自口琴中間的一條線。那條名字上的刪除線對我來說,就好像舞者被口琴和膠紙封著嘴,人的聲音被封住的感覺。我問,膠紙封著口琴,又如何發聲呢?原來方法很簡單,在膠紙上穿幾個洞就可以了。的確,努力想想,總有方法發聲的。

看《鳴》,似目睹混沌至極,陰陽兩分,衍化四象和輪轉,復又歸一,恰似聚散無常的現象。在一呼一吸間,跨過空間與身體的限制,以無言之聲,昭示人的本質。縱聚散無常,氣息永在;雖閉猶鳴,呼聲不絕。互勉之。
相片提供:西九文化區
(註)筆者觀看的是2月17日晚的一場;地點是香港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